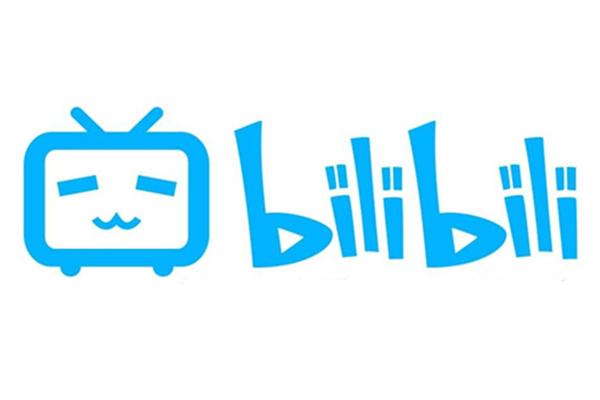01 被裁后,薪资翻了三倍
裁员的大刀终于还是落了下来。
在这家互联网大厂做了5年的短视频主管,今年4月,袁大伟收到了裁员通知。
这个消息不算突然,早在半年前他就有预感了。公司的业务板块逐渐收缩,不少项目关停,人也走了大半。最后这段时间,部门基本没什么工作能交给他了,他每天坐在工位上倒计时等着拿赔偿,想着等被裁后先休养一段时间再出来找新工作。
可真到了离职的时候,情况却和他想的不一样。
没歇多久,前司的老员工就陆陆续续找上他,问愿不愿意接活儿。袁大伟的主要工作是视频拍摄、剪辑和后期包装,前司人手不够时就会找他应急。
从正职转向外包零工后,外出拍摄半天的活儿,就能拿到5000块钱——这个定价并不是统一的,具体单价要看工作量和紧急程度。但无论如何也比正职时拿的工资高不少。
需求并不全来源于老东家,也有的私活是前同事介绍的其他甲方需求,通过同行的人脉网找到了他。5年在职经验积攒下的人脉,在离职后开始发挥作用了。6月份,他赚到了和在职期间同等的收入,8月份,他接到一个大项目,入账直接翻倍了。
和袁大伟相比,露露做自由职业的时间要更久一些,去年2月她就辞职出来了。一开始她没想长时间做自由职业,只是在之前的工作经历里受到老板的压榨和PUA,不想太早回到职场环境。2022这一整年,她接了一些零零散散的策划工作,也算能维持温饱状态,总好过全职时每月8000块的固定工资。
而2023年一到,情势却突然好了起来,她一下子接到了两个大型项目,一次能做半年,近段时间都不用为收入发愁了,“说实话,虽然大家都说今年的经济大环境更差一点,但我反而是今年更忙一些了。”
类似文案、策划、视频等专业技术性质的工种,越来越多的从业者在离开公司正式岗位后,凭借专业技术能力和社会关系网灵活就业,且收入水涨船高。
在各行业预算普遍收紧的情况下,为什么这么一小撮灵活就业人员反而赚到了更多的钱?这倒也不难理解,一些企业里的边缘部门或需求量少的业务,在精简人员后,这一部分需求自然就溢出到了海量的零工市场。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金斯在《创意生态》一书中这样解释“创意者经济”的发展,在互联网技术的助推中,我们进入了一个人人都可以是创意者的时代。一般用户、非科班出身的创意者们也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创意的价值交换——互联网文化产业的本质即是优质的创意内容,普通用户也可以零工的形式承接这部分工作。
26岁的视频后期技术工林锋,今年4月主动请缨,上了前东家的裁员名单。
这是一份事少钱多的神仙工作。林锋入职这家身处新一线城市的新能源企业,是在去年年中,头衔是视频部门主管。虽然真实情况是整个公司只有他一个人负责拍宣传片,但实体公司的内容需求并不多,来了不到一周时间,他就把公司所有的产品都拍摄完了。剩下的时间呢?能干的活儿依然很少,每天喝喝茶,和同事聊聊八卦,一天就过去了。
但林锋的不安远远大于愉悦:“上班的时间过得又快又慢,你能理解吗?上班一天熬的时候觉得挺慢的,熬过去了回去往床上一躺,第二天又上班了,周六周日放松一下一周没了。但是再一回想,好像啥也没干。”
他每次跳槽,都是出于对行业前景的担忧。2022年时他尚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工作,明显感受到工作量越来越小,公司承接的项目越来越少了,是不是要走到头了?待在这里还有没有发展?
新能源企业的这份清闲同样让他嗅到了“危险”,果然刚过半年,他就听到风声说公司资金周转不开要裁员了。其实林锋本来不在裁员名单上,少了他,公司就没有其他能拍视频的人了。他就跟组长商量,“我一个月拿一万多块钱,一个月能有两天的活儿干算好的了。留在这继续摸鱼,你不如把我裁了。”
被裁不久,他跳进了自由职业者的大海。他在BOSS直聘上刷到深圳电视台的一个外包项目,跑过去坐班剪了一周半视频,赚了2万块;再后来刷到某五*科技公司的宣传片,熬了几天大夜,入账五位数的劳动报酬;同时他还间歇性地为几家自媒体工作室承接大大小小的剪辑需求。
离开公司的束缚后,他终于感受不到经济下行的惶恐了,那种时时刻刻觉得“这X公司要完蛋了”的危机感消失了。零散的兼职倒是数不胜数,活儿是不缺的。收入好的时候,单月入账能翻三倍。
02 零工猎手,总能持续赚到钱
干了3个月自由职业,林锋感觉时间过了很久,上班都好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比起每天打卡、单纯挂靠在公司,现在他的工作模式变成了3-4天极限上工,再舒服躺上一礼拜。累是真累,赚也是真赚,这种只为自己奋斗的个人实现感也让他更开心,能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是*。
像他这样的技术型零工,通常会开拓很多找活儿的途径。*是传统的兼职招聘软件,BOSS直聘、前程无忧等,看到合适的工作他都会去沟通一下,有时也会有雇主找上门问有没有档期——但这种方式就像大海捞针,10个里面碰巧能有1个合适的,大多数都不欢而散。比如一位主动询问接不接活的雇主,一个项目1500元,一天做30条短视频。林锋很不屑:“这种东西你看一眼就不用管他了,理都不用理他。”
第二是通过同行社群,他加入了几个付费社群,经常会有雇主在群里找人,如果这月没接到什么活儿,他就会到社群里碰碰运气,虽然也是鱼龙混杂,但毕竟是付费的信息库,还是比广撒网靠谱一点。
第三种方式则是最稳妥的,朋友介绍。林锋圈内的人脉资源大多数是通过前司老东家积攒起来的。离过三次职后,老东家的外包项目对他而言倒成了一座富矿。4月离职以来到现在,林锋还能源源不断地收到前司的项目邀请——也包括这家新能源企业。后来他们发现公司确实不需要为了宣传产品单招一个全职岗位,转成外包是更有效率了。
本质上零工经济是计件制。自由职业者受到行业领域、人手、资源的限制更少。当公司很难在短时间内掉转车头做出重大决策调整时,个体户却可以。
露露这么解释打零工的抗风险能力:“对一个很宽泛的自由职业者来说,你想做美妆、时尚还是零售、汽车,我觉得这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大家都在说经济环境特别差,但即使再差的时候也总有那么一两个行业是在赚钱的,比如说经济好的时候,可能有99个行业在赚钱,经济不好的时候只有10个行业在赚钱,那我们只要去赚这10个行业的钱就可以了。”
他们能在短期内解决企业无法覆盖到的需求,再立马跑路去供应下一个有需要的人,对他们来说,这种即插即用的“U盘化就业”模式更适合在这个时代生存。
在1920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即采用灵活用工的方式缓解就业压力,直到2022年,根据全球自由职业者Upwork的报告,超6000万美国人都在做自由职业,占到整个劳动力人口的39%。而在国内,灵活用工也渐渐成了一种趋势,截止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占到2亿人。
“钱就在那,而且钱一直在有,挑战只是你能不能找到一个能让你和市场进行交易的中间桥梁,能不能找到一个靠谱的人、老板或者公司。靠谱的零工猎手永远能持续找到钱在的地方。”露露说。
另一件有利于自由职业者的因素是,在大厂裁员的背景下,互联网公司都变成了保守主义做派,更倾向于把需求交给知根知底的老熟人。
露露参与过一家互联网头部大厂的策划比稿,脑暴会从早上10点开始一直开到晚上8点,她累得脑子都不转了,公司的其他人还是眉飞色舞地提出新的创意。这个策划她改了好几版,虽然会上对方表现得很满意,最终她也没有拿下这个项目。
想不通,她就去问对接人原因,对方是这样告诉她的:“既然这个东西没有200%做出多么大的创新来,那我们倾向于更稳妥地用原先的团队。”
比起冒险追求那10分的创意进步,如果提案没有惊艳到颠覆的程度,平台会更倾向于保险,使用过去有合作经验的团队。露露想,确实是这么个道理:“他们有他们的靠山,我也有我的。”毕竟现在她承接的项目也都来自于以往打过交道的客户。现在大家各自吃自己盘子里的蛋糕相安无事,都维持着一个相对稳定的温饱状态。
但她也感到恐慌,开拓新的甲方关系是越来越难了。对于自己这样工作年份不长、话语权不高的年轻小将来说,未来要仅凭借自己的创意和技术能力来赢得甲方的信任,将变成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更严峻的形势是,对于他们这样的熟练技术工来说,想重回正职岗位也很不容易。
袁大伟的体感是,互联网公司的业务逐渐饱和,已经不需要再招高级别的主管岗,他听说,一些互联网公司更想要“便宜好用”的应届生。对入职大厂的应届生来说,未来他们可能会拿着和往届一样的工资,却承担着更高级别的工作。
最近,袁大伟给互联网公司投出的正职简历得到的回复都很少,反而是一些传统企业有回复,但在HR电话联络完意向后又都石沉大海:“我估计可能是我要价太高了,我出去都说底线是20k。”
用互联网公司的人才定价去面试传统企业,失败是可以预见的。他这样分析自己的处境,互联网公司是靠内容创意类工作赚钱的,但在传统实体企业,这些都属于边缘部门,他们本身也没有那么多内容需求,肯定给不出和互联网大厂一样的薪资。所以现在他变成了佛系求职,“有合适的就找,没合适的就算,但如果今年要继续找正职工作,我肯定会换个赛道。”
想找到心仪的工作不容易。做大厂的外包零工是一种被迫存在的状态,但它可能确实是现阶段的*解。
03 降本的厮杀
做零工收入翻倍后,袁大伟一度想着做些投入——把裁员赔偿款拿出来,专门为自己购置一套专业摄影器材。
他算了一笔账,现在做拍摄私活,器材租赁是最贵的。要租到好品质的设备,相机、镜头、稳定器等等加在一起,一天外拍的成本就要700块。如果打定主意做自由职业,越早买下器材越值得,以后能cover掉不少成本。
犹豫了很久,他还是决定再观察一段时间:“毕竟我现在只能靠原来的‘衣食父母’给活,不知道这个收入状况还能维持多久。”
为了争取到更多活儿,这些“创意工人”们普遍都有这样的感受:干得更卑微了。每个来之不易的项目都要珍惜,在甲方面前,腰杆也不敢挺那么直了。以前甲方发来的反馈露露总是会努力沟通两把,是不是对方会错了我的意思,这么做会不会更好。“过去你说改我就是不改,但现在就是好好好,改改改,你说的都对。”
虽然大厂预算收紧后更愿意找信赖的人,但反之也意味着,他们更好压榨这些“亲信”的剩余价值。
袁大伟最近沟通了不少甲方,没少因为成本的事和对方吵架。“大家能拿出来干活的预算少之又少,比如说本来一个宣传片,前几年正常企业10万、20万这种档位去拍一个,现在我觉得10万都拿不出来,就七八万就想拍,两三万、三四万都想拍这种感觉。”
在他的体感中,能接到的活儿绝不算少,但里面闲七杂八的事是越来越多了。上游供应商总能从各种意想不到的渠道节省成本。有一次他租了300元一天的相机,在他看来器材租赁是刚需,砍掉这一块的预算势必要牺牲视频质量。但供应商告诉他,30元一天就可以了。“他不在乎,那我也不在乎了。”
还有一次,他给甲方的报价和往常一样,但直接被对方砍掉了一半。两边协商了许久,最后达成协议,甲方只出一半的钱把拍摄部分外包给他,至于后期,他们会另找人完成。再后来,袁大伟就从其他渠道听说,他们找到了两个线上实习生,用500块钱解决了所有问题。
甲方爸爸们要压成本,他们自然也要想方设法帮忙压低成本。有了上次被撬活的经验,袁大伟决定一定要和同行好好学习一下成本是怎么把控的——等同行的片子出来后,他发现这压根不用学,一看成片的质量他就懂了。“垃圾,就两个字,垃圾。”自然客户也能看出来视频质量变差了,发来不少修改意见。袁大伟气不过,又跑到自己的中间人那吹耳边风:“你看,你这个价位是不是弄不出好东西。”对方也很为难:“我也觉得这样不行,但是客户成本摆在那里,没办法。”
他这么概括今年的零工市场:“饿狼太多了,一块肥肉摆在这,本来一个人吃下来就很好,但是总有人跟你恶意竞个价。”要价更低的人半路杀出来截胡,“降低成本”的诱惑无疑是巨大的。
为了提升自己在零工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多次,林锋都抱着亏本接活也要弄好的决心。不仅如此,每次零工做完,他还要给甲方爸爸寄一点礼品打点关系。“为的就是让他下次有活时还能*个想起我。”他觉得寄出去的礼物确实是管用的,这不,回头客不少,这几个月的生意都不愁续弦。
零工市场上也呈现出了僧多粥少的局面。在小红书上随处可见找活和求活的帖子,在那些“零工经验分享贴”下,如果多出一个甲方问“接活不”,下方往往会盖出10层楼问“还缺人吗”“私”。没有公司的稳定庇护,自由职业者们陷入到最原始的市场厮杀中,被裁后的红利能持续多久,真的说不好。
做自由职业以来,林锋经常处于一个很想上班,又很不想上班的挣扎状态。最近他的焦虑直线上升,虽然自己暂时赚的越来越多,可非常不确定未来还会不会有这么多。有钱赚的时候他们还会对不同性质的工作挑挑拣拣,看看上游需求方是不是明白人,和他们沟通顺不顺畅。可现在也不太敢挑了,生怕哄不好甲方爸爸,又一个“销售线索”失联在人海里。
你说,干外包零工的自由职业能长久吗?这个月接了某大厂的纪录片外包项目后,林锋挣的钱至少够吃到明年,当时他确实拍着胸脯说没问题。
“但如果你下个月问我,我可能就是另一套说辞了。”沉默了一会,他补上一句。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图片由受访者提供或网络)
【本文由投资界合作伙伴后浪研究所授权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editor@zero2ipo.com.cn)投资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