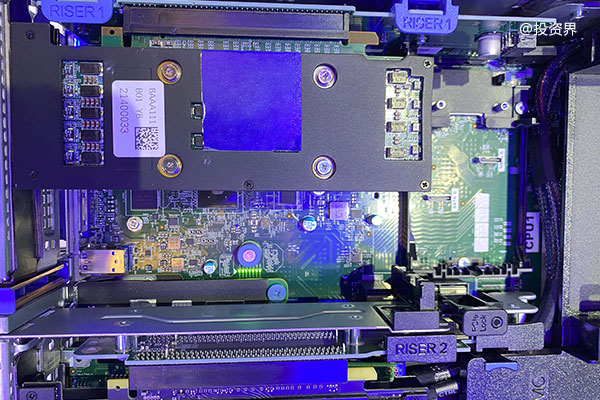日本经济恢复通胀、日本公司治理改革的持续发力、低利率环境,种种因素都激发着全球投资者对日本市场的兴趣,成为亚太市场中PE投资金额增速最快的区域。然而日本并购市场及其并购基金生态能有今日之发展,实则是漫长积累与演进的结果。
日本三次并购浪潮的演进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日本企业掀起了首轮大规模并购潮,并且以海外并购为主要形式
19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因广场协议(1985年)后日元大幅升值和国内资产泡沫膨胀,进入“黄金时代”。企业手握巨额外汇储备,国内投资回报率下降,叠加美欧贸易摩擦加剧,日本政府将战略重心从“贸易立国”转向“海外投资立国”,鼓励企业通过并购获取技术、品牌和市场渠道,同时转移过剩资本以缓解国际压力。这一时期三菱地产收购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索尼收购哥伦比亚影业等标志性交易接连涌现。此阶段并购显著提升了日本企业的国际存在感,但由于许多并购基于投机逻辑失败案例也不少见。比如三菱地产以13.73亿美元购入纽约地标性建筑洛克菲勒中心,然而由于曼哈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实际租金收入远低于预期,加之日元升值和美元贬值的影响,导致形成投资损失。
随着泡沫经济破灭,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进入以产业重整为核心的第二次并购周期,私募股权基金开始出现
面对资产负债表衰退和产能过剩压力,日本国内开始了大规模的横向整合,同业企业合并从而提升规模、增加效率。日本许多支柱企业都形成于这一时期,例如,三菱东京金融集团与UFJ控股的合并,成立了全球*的金融集团之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三家大银行合并成立了瑞穗控股集团;两家拥有百年历史的“三共株式会社”和“*制药株式会社”合并成立了*三共株式会社的前身。
这一时期,日本企业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和全球化竞争的压力,考虑剥离非核心业务或进行重组,为私募股权基金(PE)的发轫提供了机遇。日本最早的PE机构Advantage Partners 于1992年成立,并于1997年推出了日本首支本土并购基金,开启了日本私募股权市场的先河;Unison Capital成立于1998年,首支基金于1999年募集完成。
对于外资基金而言,危机也打开进入日本并购市场的大门。日本战后长期奉行产业政策和交叉持股的模式,使得外资很难参与到企业的控制权交易。危机下收购不良资产和重组企业的契机成为外资PE切入日本的契机。美国擅长困境收购的基金Ripplewood于2000年收购日本长期信用银行(LTCB,当时主营长期工业贷款,累积了大量不良债权,后重组更名为新生银行),成为日本首例外资控股收购金融机构的案例。Lone Star基金于2001年收购因不良债务破产的东京相和银行(后更名东京之星银行),通过注资、剥离坏账、调整业务等方式,将一家地方银行重塑为新型零售银行。这一阶段日本政府因银行体系危机而开放金融业予海外资金救助,围绕金融业聚焦困境收购成为外资PE在日本开展并购的主要逻辑。
2000年往后,日本政府继续放宽对外资的限制、同时完善并购相关的政策,受到亚洲市场以及政策的吸引,海外PE开始更积极的布局日本市场,凯雷、Bain Capital、KKR等全球基金纷纷在日本设立办事处。海外PE涉猎的行业也从金融业拓展到电信、制造、服务等领域。比如,2002年凯雷从日本零售巨头大荣集团手中收购了朝日安保株式会社(Asahi Security Co., Ltd.);Bain Capital在2009年收购了日本*的呼叫中心和电话营销外包服务公司贝尔系统24株式会社(BellSystem24)。
这一时期,日本的私募股权基金投资金额迅速增加,在2007年达到阶段性峰值1.7万亿日元,较2000年增加了7倍,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的并购并购活动有所减少,部分外资私募股权基金面临融资困难动作也放缓。
2012年后“安倍经济学”出台,公司治理改革推动并购市场活跃
进入2012年后,日本政府推行公司治理改革,期望通过改革解决交叉持股、主银行制度等历史原因导致的企业治理僵化和效率低下的问题,2015年日本政府出台《公司治理守则》鼓励上市公司将现金转化为ROE,提升股东价值增强股东回报。政策的强力推动打破了历史上日本企业交叉持股"内部协商”的经营方式,日本企业通过分拆非核心业务提升ROE,借股权结构调整进行市值管理动机日渐强烈。而外资进入日本资本市场后,激进投资者的出现也增加了上市企业的外部压力,从而催生了部分企业私有化、MBO的需求。在政策的引导下,2016年大型并购交易带动日本并购市场迅速回暖,总交易规模达到1.1万亿日元,同比增加175%。
而随着市场的发展,PE的交易方式和交易来源也愈加多元化,要约收购、敌意收购、PE间交易等方式开始出现。例如,Unizo Holdings Co., Ltd.一家主营商务酒店和不动产租赁的上市公司遭遇本土日企敌意收购时,黑石曾尝试通过敌意竞标收购Unizo,但最终由美国基金Lone Star联合管理层完成了私有化。欧洲私募股权基金Permira Advisers收购的日本回转寿司连锁品牌“寿司郎”,交易对手方为帮助寿司郎完成MBO私有化退市的本土基金Unison Capital。
日本并购市场及PE的发展主要依靠外力驱动
虽然日本企业海外并购方面经验丰富,但在接受“被并购”以及PE方面,其态度与其他国家仍存在显著差距。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等制度塑造了企业和员工间强烈的情感纽带,而日本社会对“企业共同体”的认同感也极强,强调对利益相关者友好的经营理念,这导致企业被并购时会遇到员工、工会甚至地方社会的反对,甚至企业主视被并购为失败。在经营理念上,日本企业普遍看重企业的长期发展、重视社会责任,对财务投资人持有一定时间后出手和降本增效的策略存在冲突,这也导致日本社会对PE类财务投资人持有一定的戒备心。
这一文化特点导致日本并购市场及PE发展的关键转折主要来源于危机、政策等外力。首先,上世纪90年代末,企业遭遇经济危机经营陷入困境,不得不考虑整体出售。其次,2010年后政策助推作用凸显,安倍政府推动的《公司治理守则》强制要求企业优化资本效率,东京证券交易所2023年要求市净率低于1倍的公司披露并实施改善措施,直接倒逼低估值的产业巨头加速剥离非核心资产。而改善并购环境、为外资创立友好投资环境等政策则导致积极投资者的增加,激发了企业的市值管理动机,也间接导致企业出于外部压力寻求私有化或MBO。政策改革是日本并购市场发展的关键推动力,也形成了日本PE交易主要由超大型并购交易组成的特点,2020-2023年期间,日本市场金额10亿美元以上的交易占比约65%,而同期亚太其他市场的占比约30%。近年来,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代际传承压力也被期待成下一个并购市场发展的助推因素。到2023年日企社长的平均年龄达到60.8岁,70岁以上的占比约25%,
在外力的助推下,日本并购市场和PE的活跃程度正在逐步提高,2019年-2023年日本并购金额占GDP的平均占比为3%,其中有PE机构参与的并购金额占GDP的平均占比为0.4%。相比2014-2018年分别增加了50%和100%(2014-2018年,日本并购金额占GDP的平均占比为2%,其中有PE机构参与的并购金额占GDP的平均占比为0.2%)。虽然同比改善明显,但和其他市场相比,日本并购市场的活跃度仍然有继续提升的空间。2019-2023年同期美国、韩国市场并购金额占GDP平均占比为9%、5%,有PE机构参与的并购金额占GDP的平均占比为1.3%、0.5%。
外资PE适应日本市场需要时间沉淀
疫情之后日本市场以其独特的结构性机遇吸引了不少海外投资人的注意力,这背后不仅是对亚洲市场的战略再布局,也源于日本本身所展现出的独特吸引力与结构性机遇。其一,在宏观经济层面,2022年以来,日本通胀水平重回2%以上,企业和消费者的通缩预期开始逆转,通缩预期的逆转以及企业盈利能力的修复无疑也提振了海外投资者进入日本市场的信心。其二,日本制造业中存在大量技术*但管理保守的家族企业、人口老龄化结构下医疗和养老市场需求及企业传承需求旺盛、传统企业渴望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等等因素都为并购基金储备了良好的投资机会。其三,日本政府与东京证券交易所近年来持续推动公司治理改革,鼓励企业提升资本效率,“真诚考虑”收到的收购提议,积极投资者占比逐渐提高。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开始重视股东回报,主动剥离非核心业务、优化资产结构。这一系列改革不仅提高了企业透明度,也为并购基金的介入提供了更多可操作空间。相比以往,日本管理层对于外部资本的态度更加开放,收购谈判的阻力正在降低。
然而,日本对外资的态度向来谨慎,对于尝试开拓日本市场的海外PE而言,也有其需要解决的本土化难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显示,日本外商直接投资(FDI)存量占GDP比重长期低于5%,不仅远低于美欧的30%-40%,甚至落后于印度、印尼等新兴市场。2024年加拿大Alimentation Couche-Tard收购7-Eleven母公司Seven & i的提案,因涉及8.5万家门店的运营网络,也被日本政府以“灾害时期民生保障”为由划入国家安全审查范畴。这种“选择性开放”使得外资并购核心资产时会面临更大的障碍,曾经引得数家海外PE争夺的东芝最终也是接受了日本本土阵营JIP(Japan Industrial Partners Inc)的要约。而且即便是合规交易,来自舆论场的压力也可能对并购进程形成阻碍。
在日本有影响力的外资私募股权(PE)机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积累过程。一方面,日本作为东亚国家,其商业文化注重长期声誉积累与关系网络构建。外资机构若想进入日本市场,不仅需要构建高度本土化的团队,建立当地关系网络,还需要时间来积累在本土商业环境中的信誉。另一方面,日本社会曾长期对外资私募股权基金抱有“秃鹫资本”的负面印象,尤其是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期,当时外资基金通过收购不良资产获利,被公众视为在经济衰退期间“掠夺日本企业”的代表。在过去二十余年中,外资基金通过强调共创价值,在日本经济“再生”过程中展现其优势和价值,从而逐步重塑了其社会形象。据日本经济产业省调研,PE基金参与的并购交易在企业引进国际先进管理经验、高端人才,优化组织结构和激励机制,以及拓展海外销售渠道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文由投资界合作伙伴微信公众号:晨壹投资授权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editor@zero2ipo.com.cn)投资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