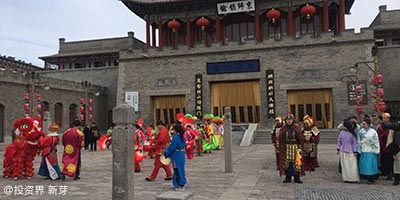精神力量是宋庄艺术家们最被高估的品质,生存压力则是他们最被低估的东西。
在中国宋庄,生活着将近两万名艺术家。他们从事的艺术门类包罗万象,其中以绘画居多,宋庄也因此以“画家村”知名。熟悉此地的人通常会在这时纠正:画家村主要指的是小堡(pu)村,而宋庄是个镇。与此相应的另一句更具官方色彩的话是:宋庄是中国的,小堡是世界的。
1.基层干部为生计谋
宋庄镇隶属于北京市通州区,与徐辛庄镇合并之后,辖域面积变成了现在的115平方公里。这个数字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155平方公里相差无几。不仅面积相近,在地理位置上,宋庄镇也紧邻副中心。小堡画家村与即将投入使用的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直线距离仅有区区4公里。
官方披露的数据显示:2016年,小堡村上缴国地两税9630万元,人均收入6万元。同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为9万元,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万元。
而在1993年,小堡村村委书记崔大柏根本想不到这弹丸之地会化作今日盛况,这位党的基层干部彼时正在为如何带领村民致富而寻方问道。和那个年代有生意头脑又关注时势走向的能人一样,他已经深深地意识到一个真相:与工业生产相比,“土里刨食”无法迅速带来商业收益,而村民们最宝贵的商业资源就是他们守着的大片集体土地。
土地可以租给个体工商户,工业大院由此聚集。但这仍然不符合崔书记对于未来的想象,这个村庄需要的不只是物质财富,还有精神力量。比如知识、思想、文化素质。
画家群体,似乎符合“精神力量”这个标准。
关于画家是如何在小堡村聚集起来的,一直流传着不同版本。有的说是画家自己找来的,有的说是村里请来的……这些说法并不准确。
按照官方说法,当年一位通州籍的艺术家目睹圆明园艺术区被强行遣散,遂四处打听,希望给这群被视作不稳定分子的画家朋友们找个落脚之地。正好他的一位亲戚是小堡村人士,家中闲置有破落小院一座,这亲戚听闻竟有人愿出钱,欣然允诺。
就这样,*批画家落脚小堡村。对于画家而言,小堡也有得天独厚的吸引力——远离市井喧嚣五十公里以外,院落虽破败不堪但租金十分便宜,院子较周边村落更为宽敞。村民和画家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我们知道,在中国,外来人口要在一个农村里成群生活,仅凭呼朋引伴并不足够,关键在于基层组织的态度。
如果画家的选择仅是火种,那么崔书记的态度,则是小堡村最终演变为画家村的炉膛。多年以后回看,小堡村在经济发展上一直不落人后,也正出于这位基层领导人出色的商业头脑和开明的经营策略。
画家群体常被视作异类,但不少人有大学学历,这个细节让崔书记很快就作出了“接纳”的决定。就这样,大面积的集体土地被以一纸协议长租给个体工商户,小面积的宅基地和房产则允许村民或租或卖给了艺术家。
这种盘活土地的思路,今天看来不足为奇,可是在当日,却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作用。最重要的是,需要一种带有“犯上”意味的勇气。大概由于小堡村地处偏远,与河北省仅一河之隔。也大概由于这位党的基层干部为生计谋,本能地划定了符合村民利益的标准。
2.产权不清惹的祸
小堡村的艺术生意不胫而走。
不少有经济实力的画家更是以买代租,一纸契约买断了村民的房产。这种情况在小堡村非常普遍,在当时看来两厢情愿的生意,却埋下了十年后双方对簿公堂的种子。
显然,一切都是因为利益。
自2006年起,购买村民房屋的10多户艺术家被陆续起诉,村民以买卖合同无效为由,要求收回曾经售出的房屋及院落。这其中最典型的诉讼是“李玉兰购房案”,法院在审理案件后于2009年作出了判决,这份判决即便在司法流程已相对成熟的今天来看,依旧体现了当年的司法机关高超而精妙的处理手段。
判决可视作三部分:*部分,判决双方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村民返还李玉兰9.4万余元;第二部分,李玉兰腾退房屋,还给村民;第三部分,也是最关键的部分,认定村民为导致协议无效的主要责任方,按七三开承担责任。随后经过评估,房屋现价为26.47万元,依此价格的70%计算,确定村民向李玉兰赔偿18.5万元。共计向李玉兰支付约28万元。
这份判决的精妙之处在于,既维护了现行法律禁止农村宅基地与房产自由转卖的条文,又考虑了房地产升值的现状,将历史遗留问题放在当下现实中进行了平衡。如此一来,村民们若想违背十年前的契约就需要掂量一番,因为不仅要返还购房者当初的房款,还要按照现在的价格再加一笔钱。很多村民拿不出这笔钱,自然就不了了之。
归根结底,乃是由于我们国家对于土地产权的严格控制。众所周知,中国的土地分为国有与集体所有。所谓国有,就是国家的土地,通常在房地产招拍挂中卖出天价的土地,即属此类;所谓集体所有,就是自然村庄占有的土地,其中包括了农民盖房的宅基地。此类土地不允许面向社会公开售卖。
这种产权制度的初衷是确保国家占有充足的生产资料,同时让为数众多的农村人口有条件地占有他们世代居住在此的生产资料。艺术家们当初在宋庄的房产买卖大多出于一种朴素的买房置地意愿,加之价格不高,买了也就买了。可是房地产在过去这二十年火速升温,原本价值十万元的院落如今翻了好几倍,以及有可能存在的拆迁补偿,都让村民产生了反悔的动机,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种买卖行为本身就不受法律保护。
若是农村集体行为,还有集体的信用作为保障,比如全国规模*的集体产权小区、同样坐落于通州区的北京太玉园,尽管买房者也知道不受法律保护,但那是村集体的售卖行为。可若是从村民个人手中购得,情况就复杂多了。我们知道,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个人行为更容易也更便于动摇。
3.更多的冲突
艺术家们在小堡的牧歌田园生活,就此闹的沸沸扬扬。十年前受到行政力量驱赶的他们,此时又不得不面对经济利益与制度未有涉足的灰色地带。
最终,为了尽可能全面彻底地解决房产纠纷,崔大柏又开动了他那富有个人魅力的头脑,在村庄范围内重新组织规划了一片区域,专门用于艺术家居住工作。今天的画家村,也由北向南被分为三个特色鲜明的区域:艺术家聚集区,工业大院区,村民宅基地。
但个人的力量再强大,也无法彻底改变人性。画家与宋庄的冲突,也绝不只限于房产纠纷。包括当初被崔大柏乐于接受的画家们的“精神力量”,也在此后的多年间饱受质疑。
2018年5月的一天中午,画家村最负盛名的艺术餐厅一条街“小堡南街”,此地也是小堡村委会所在地,发生了一件小事。在一家名为“圆味”艺术餐厅的门前,几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打扮的客人用餐完毕,聚在一辆售卖樱桃的平板车前朗声谈笑。贩卖樱桃的是一位本村老太,她紧张又急切地和客人攀谈,希望做成一笔买卖。然而,客人却并不着急,反而作势要抓取一把樱桃尝尝味道,老太只好死死护住。见状,客人们反倒发现了新的乐趣,他们不断作势抓取樱桃,老太屡屡上前护住,看到老太狼狈不堪的样子,客人们哈哈大笑。
若非笔者亲眼所见,断不肯相信这是发生在中国北京宋庄这片艺术家园里面的事情,倒更像是影视剧中所描绘的流氓无赖戏弄小摊贩的可耻桥段。老太随后的一句话也道出了这种违和感:“你们都是艺术家,怎么能这样呢?”
这实在是一种深深的误解。
在很多人的眼里,艺术家本该素质超然、不食人间烟火,可是他们转脸就得为了房子、拆迁、利益而斯文扫地。如果说这样的斯文扫地乃是由于制度使然,那么另一个常人并未深入洞察却普遍存在于所谓艺术人群身上的真相则是由粗鄙的人性使然:一些艺术家们在很多时候对自由怀有某种粗暴而自私的联想,并由此时常陷入刻意破坏的个人行为中。也因之,不少打扮成艺术家样子的人并不总是温文尔雅,相反,他们被看似毫无来由的愤怒和玩世不恭所包围。
宋庄若有糟糕的地方,则首推那些以艺术家之名行流氓无赖之实的大小事件了。这些事件,从1993年艺术家们来到宋庄直至今日,从未消弭。
最早的冲突即源于这种深深的误解。村民认为奇装异服的艺术家们群聚喧闹,不是好人,根本就不是有文化有思想有精神力量的人,艺术家们则快意恩仇,不受管教。当曲高和寡的艺术家们卸下作画时的娴静圣洁,再借助二两黄汤,肚子便饿了,村民的财产就要遭殃,比如家禽、庄稼。这样的事情,即便在公开的报道中也并非罕见。
另一种冲突则是由于艺术家们更为出格的行为导致,有的艺术家当众脱光了衣服展示身体,每逢宋庄举办艺术节就更是如此。客观而言,裸露身体是一种自由,但是出于某种目的而在某些特定的时刻裸露,即便是以艺术的名义,也让人觉得莫名其妙。最关键的是,艺术这种极度需要创新精神的领域内,裸露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若仍热衷于此,实在让人提不起兴趣。
但是生活在宋庄的原住民们比外人更在意此类事件。由有关部门主抓、村里的联防队负责协助的“管制行动”很快就来了,他们把这些“捣乱分子”抓了个遍。此类冲突也一度成了艺术行为的一部分。就像那些希望青史留名的人,故意激怒当局从而实现因言获罪的“名声”,这本身就充满了虚妄的味道。
4.可疑的精神力量
艺术家有穷有富,人性有好有坏。但我们往往习惯于给人们贴上统一的标签,认定艺术家都是纯良之辈,这种先入为主的片面标签,乃是种种误会产生的根源。
一位名叫何路的艺术家自费出版了文集,里面收录了一部长篇小说和八首长诗。书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没有书号,没有出版商,售价为两百元。
这本书如同一个隐喻,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生活在宋庄画家村的艺术家的状态。只有当你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才会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这个群体的精神世界——充满了对于“不公”“欺骗”“丑陋”等话题的描写,可如前所述,这群人有时候也会做出同样丑陋的事;处处流露出无力改变亦无法接受现实的消极情绪,既缺乏直达本质的批判,又充满自以为是的软弱;充斥着对男女性爱的毫无想象力的生硬表达,传递出并不高明的价值取向;最关键的是,通篇以自我为中心,全无对于客体世界的善意或爱意。
即使常人也能观察到一个现象:一流的艺术家,在表达思想的时候并不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样做除了表现自私之外并没有任何令人共鸣之处。而一批知名艺术家和背后的商业机构对“玄学”的过度追求使得很多有志于从事艺术的人产生了误解,认为艺术就是要标新立异、情绪鲜明、有话题性,*叫人看不懂,并因此振振有词,躲藏在不知所云的表象之下,假装很有思想。
宋庄的很多所谓艺术家,皆属此类。但这并不影响这个生态的运行,在顶层是少数几个在国际上有知名度的当代艺术家,比如方力钧、岳敏君;中间是一些有商业渠道和人脉网络的艺术从业者,*层则是两类人:一类是有艺术功底、以出售作品为生的年轻人,一类是欺世盗名的伪艺术家。这个生态的长期运行,使得所有这些人都有其生存空间。
作为官方机构,如何管理或服务这个生态成了小堡村的头等大事。如果将画家村的生态视作一种商业模式,则如同所有企业需要监管一样,画家村也需要管理运营部门。在村里,这个部门就是艺术家促进会。
艺术家促进会的成立极大地改善了宋庄与艺术家的冲突状态,双方从以前的对立转变为和解。艺术家们也派出了代表,积极参与促进会组织的各种活动,比如春节团拜会、小堡艺术产业升级座谈会等等。
在座谈会上,艺术家们也展露出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对于我们身处的这个商业时代和宋庄的整体形象而言,这一面实际上是更容易被人接受的一面。
比如艺术家代表们提出的诉求:希望有医保;希望被懂艺术的人领导;希望画家们作为画家村里最弱势的一方受到应有的善待(画家们认为在当地政府、村民、乡镇企业、画家四个主要群体中,画家是最弱势的一方);不希望宋庄被商业化;不希望发展旅游业;不希望私人美术场馆没有稳定的运营资金……
显然,艺术家们关于未来的看法并不如崔大柏那样清楚,他们的诉求也大多充满了自相矛盾之处。但是艺术家们愿意坐下来说出自己的想法,已经是一种从江湖而至庙堂的进步了。也许,曾经被崔大柏寄予希望的艺术家精神力量,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不断提炼升华,最终产生出人意料的果实。
5.饮食男女和艺术生意
未来的果实也许是出人意料的,正如现在的宋庄曾经也是出人意料的——宋庄最有名的除了艺术家、美术场馆之外,就是随处可见的艺术餐厅和书画商店。餐厅和商店,就是艺术生意带来的意外收获。
以商业角度论,艺术生意不仅指单纯的艺术品买卖,虽然这是这笔生意的核心部分。艺术生意还包括一系列周边配套,比如艺术建筑、艺术场馆运营、艺术家个人品牌的培养、生活与商业街区的规划管理、相关产业与人才的引入与升级、有政府参与的商业模式引导与创新等等。
以1993年为始点,经过25年的苦心经营,崔大柏最容易被常人所触摸并理解的果实却不是上述的一系列艺术生意,而是遍布小堡村的艺术餐厅。这些餐厅别具一格,是除了宋庄美术馆之外最名副其实的艺术产品。
这种现象既是偶然所得,也是艺术区打造的必然结果。以米娜餐厅为例,这家由独立纪录片导演开办的艺术餐厅主营川菜,山城豆花和四川燃面味道正宗,另外一个特点是该店的服务人员大多是听觉与语言障碍人士,宋庄最有名的几个艺术家时常光顾该店。此时分明能感受到艺术的精神力量与人文关怀。
事实上,几乎每一家受人欢迎的宋庄艺术餐厅,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即便是同样主打川菜的另一家餐厅,冒尖川菜,虽然老板并非艺术家,却也有自己的故事,这故事便是在别的地方吃不到的菜式,比如双椒掌中宝、辣子肥肠,肥肠先用滚油炸透,再辅以干辣椒爆炒,酥脆可口。而另一家主打广式靓汤的火锅店“璞悦荟·鸡锅门”则以广东清远鸡为底料,熬出一锅浓郁清甜的鸡汤,鸡肉捞出,蘸着沙姜甜醋,异常甜美。
这里的店家取名也绝不落俗,光看店名大概是猜不到菜式的,如盘丝洞是川式火锅,春常在是云南菜,魁元是官府菜,杜鹃花开是江西菜,原品记是煲仔饭,沽酒小铺是串串香,一块豆腐是淮扬菜……
饮食男女之外,另一个常被人光顾的场所便是成片的艺术商店。这里的故事讲述的是另一个维度的宋庄——底层艺术从业者的生存状态。
在一家名为士东画家城的艺术商铺内,一位艺术品商家道出了忧虑:“现在的艺术品市场用两个字最能概括:乱、滥。比如行画。”
什么是行画?“就是工艺品,大概包括喷绘、印刷、写真。”对于用手画画的人来说,行画并非不可接受,但放在一起售卖并不科学,“政府需要对艺术品市场有正确的评价和规划,比如A区都是纯艺术、绘画,B区都是工艺画,这样才是合理的。” “而且画家群体鱼龙混杂,每年有新人加入,比如美院应届毕业生、离退休老干部。”
老……老干部?“是的。退休了没事干,就来这租个工作室,挂个美术馆的牌子。这些人会与专业画家形成竞争吗?不会,他们顶多充个人数,比如政府统计这里有多少画家的时候。”
另一位商家,笔者拜访的时候他正在专心作画,画纸挂在墙上,他用毛笔照着旁边的一幅尺寸较小的画作熟练地临摹着。
“我就是个画画的农民工,简称画农。”眼前这位男子出生于1967年,体格魁梧健壮,运笔如飞,交谈过程中目光很少离开画纸,并不影响他自如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吃饭才是最基本的。大画家不也一样吗?画画,不进则退,总得画。我也想坐办公室,有开支,那多好。咱俩在这唠,也没啥用。还是得老老实实地画。”
“有这么个地儿也挺好,要没有的话更难受。”“不过这地儿也坑老鼻子人了,我很多朋友,有俩钱了就来租个画室,败光了再走,过一阵子又来了,跟吸毒似的,有瘾。”
他的日子大抵过的不错,这间不过八平米的画室年租金五千元,而且他已经在离此不远的地方买了房。“人呐,又得老实又得精明,老板也不愿意跟傻人合作。”
生于1986年的另一位商家则代表着底层画家中的新生力量,“从小喜欢画画,外地美院毕业后来这里的,三年多了。现在的艺术品市场,无论高端低端,都不太好。甚至整个经济大环境也不好。” “这是相对的概念,通常走市场的算是低端,纯艺术的算高端。不过也不*,比如有的名家一幅画几十万,有的纯艺术画家一幅也就几万,相对来说,你几万的也算低端。”
显然,在他看来,作品的最终售价是判断其高端低端的一个重要标准。这和前文中提及的艺术家代表们全然拒绝商业化的想法截然不同。
“比如这幅70*90的油画,售价1200元左右,两天完成。这是客户预定的,他也是开画廊的。”
在这条产业链上,他相当于上游的供货商,有艺术品消费者在别的渠道看到他提供的小样或其他作品,喜欢的话就会买走,或者预定。换句话说,他的很多作品在完成之前就已经有买家预定了。
“坚持不下去的人太多了,画画很辛苦,常人以为画家都是坐在画板前面,花点时间,一幅画就完成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如果这边要清理低端产业和人口,比如一些边缘的,对于大的市场规范来说有好处,但对于他们个人而言,算是梦想破灭。”
“辛辛苦苦画出来的如果总是不被市场认可,就会影响积极性。”
总体而言,他倾向于让市场变得更规范。因为真正用手作画的人不害怕竞争,担心的是不规范。
“画画的谁不想成名成家?但那太远了。”“还是看市场吧,如果我这样的状态能逐渐稳定住,先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再慢慢转型,到时候作品风格也成熟了,就可以画一些自己想画的。顺其自然吧。”“现在的市场太差,以往正常的时候下半年好一些,算是旺季。现在基本不分淡季旺季,都很差。”
他不像很多激烈的艺术家,他对这世界没有苦大仇深,说实话,他更像一个心态平和的上班族,虽然他没有社保。
6.结语
多年以后的今日,在小堡村已经几乎看不到大规模的肢体冲突了,艺术家圈子的扩大和艺术品生意的沉浮,让这些充满幼稚激情的行为失去了诗意。在小堡村,阶层也已基本固化,年轻人们如果想在此地讨生活,首先要面对更现实的问题:租金。
在1993年,买断一个院子仅需数万元,租金则几乎可忽略不计;而在今日,小堡村的一个总面积100平米左右的小院子,年租金最少也要五六万,再大一点的从十数万至数十万不等。如果说1990年代是一个仅凭热情与天赋就能忍受寂寞等待出头的艺术时代,当时间进入新世纪之后,有志于从事艺术行业的年轻人首先要明白的道理是:有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撑你的艺术理想。
这是一个残酷的话题,也是一种新的冲突。
艺术本身和城市化之间的冲突——艺术是需要边缘化的自由空间的,而城市化覆盖小堡的时候,这种空间不复存在。也许小堡村会沦为一个没有个性的城市街区,对于村民而言,他们的生活并不会因此变坏,反而会更好。对于艺术家而言,小堡早已不是当年充满热情与试探的“法外之地”,寂寥高冷的艺术味道已被日益浓厚的城市景观取代。
若说激荡回响是艺术的题中应有之义,则今日小堡达到了一种和谐的真谛:无风无浪,波澜不惊。某种意义上,崔大柏在25年前的夙愿,早已实现了。
【本文由投资界合作伙伴微信公众号:砺石商业评论授权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editor@zero2ipo.com.cn)投资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