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年末,都是传统的“购物季”。在这一段时间里,人们讨论的最多的,就是“价格”。自从“双11”风潮兴起之后,不只是国内,国外的许多媒体也观察到中国商品的“物美价廉”。
事实上,中国商品的“物美价廉”背后,藏着深刻的文化脉络和商业变迁,我们仔细查看这些脉络,也能够看到未来的走向。
在维舟的这篇文章里,我们将回溯到过去,了解为什么中国商品的价格会这么便宜,在21世纪的今天,又如何继续提高竞争力?
欢迎来到维舟的专栏——“古今之变”,要理解现在,就必须回望过去,那不仅是塑成当下的冰山底部,还埋藏了无数曾有过的可能。
自2018年以来,“双11”已超越西方传统购物节“黑色星期五”,成为全球*的购物盛会。这一网上狂欢除了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的海量商品之外,最吸引人的,当然是其*竞争力的价格,连远在芬兰都有网站惊叹这是“全宇宙*折扣日”。
价廉物美的中国货,不仅中国人难以抵挡,外国人也一样。《中国的非洲》一书中不无夸张地说:“中国商品价格仅是其他国家商品价格的1/3-1/5。很快,家家都有了存货。对于贫困国家而言,购买便宜商品就好似吸毒,容易上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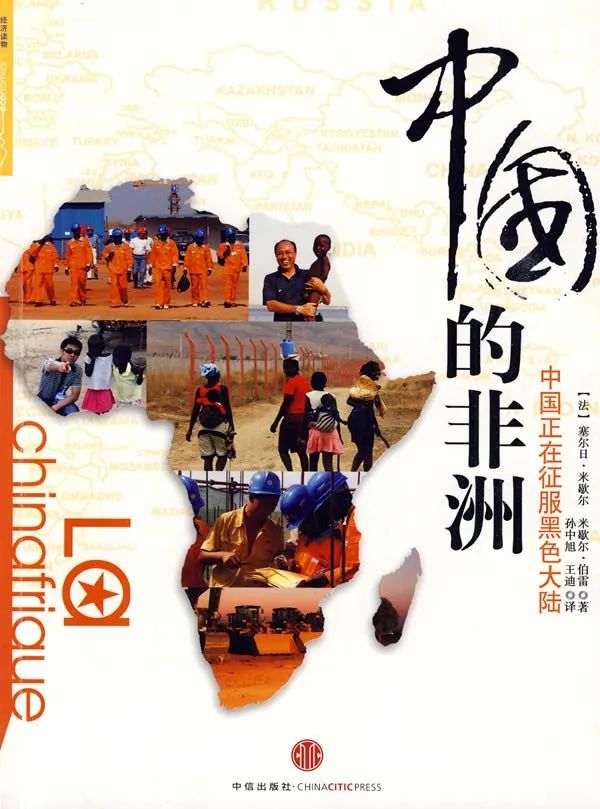
《中国的非洲》
塞尔日·米歇尔 著,孙中旭 王迪 译
中信出版社,2009-10
很多人出国后,想买点纪念品,结果往往发现当地集市上的小商品几乎全都标着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2006年,罗丰等一群中国学者去蒙古国,回国前想看看有什么当地玩意可买,结果发现除了蒙古皮靴、蒙古包外,全是“廉价的中国商品”。更早些年,历史学家冯明珠1987、1990年两度前往不丹,发现即便边境贸易全被禁止,但中国货仍然“充积市场”,根本挡不住。
确实,这些年中国货之所以能横扫全球,最重要的武器,说白了恐怕就是“便宜”二字,以至于这些年“China Price”(中国价格)在欧美也成了一个热议话题。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货为什么能这么便宜?
01、中国价格的魔力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很多人的*反应都会归功于近四十年来中国制造业的兴起、技术进步,当然尤其重要的是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鲜为人知的一点是:中国货的价格竞争力并不是这些年才如此明显,而是几百年前就这样了。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西方人有史以来首度与中国人直接做生意,除了瓷器、茶叶等中国特产外,最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就是中国货之价廉物美。西班牙人1565年才开始统治菲律宾群岛,但不出十年,中国廉价商品已涌入马尼拉。1587年有30多艘中国帆船运载大量丝绸等商品,其价格之诱人令西班牙总督简直难以置信:“他们卖得这么便宜,以致我们只能作这样的想法:要不是他们国家里生产这些东西不需要劳力,便是弄到这些东西不要本钱。”
1590年,菲律宾多明戈主教(Friar Domingo)在呈交西班牙国王的报告中说,在马尼拉的中国人不仅能制造比西班牙所制造的“更漂亮的物品,同时,有时候这些物品是如此便宜,不好意思提起”,而且“这些人是如此熟练和聪明,以至于他们一看到西班牙工人制造的任何物品,就能精确地复制”。
在当时的国际丝绸贸易中,中国货横扫全球,几乎没有对手。价廉物美的中国丝织品被船运回美洲后,迅速占领了墨西哥市场,西班牙殖民当局在给国王的报告中承认,从智利到巴拿马的美洲各地到处都能看到中国价低质优的中国丝绸,其售价仅为本地所产丝绸的三分之一。
《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总结说,中国货“很快就结束了西班牙商业利益对该地市场的支配”,因为西班牙商品根本无法与之竞争。1594年,秘鲁总督写信给马德里的政府当局说:“中国商品如此便宜,西班牙商品如此昂贵,以至于我相信不可能将这种贸易扼杀到没有一件中国商品在这个国家消费的程度。既然一个男人能让他的妻子只花200里亚尔(合25个比索)就穿上中国丝绸,他就不会花200比索给她穿西班牙丝绸。”

《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
崔瑞德(编) 牟复礼(编),史卫民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2
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丝织厂全部倒闭,连经营美西贸易的商人也因损失巨大而破产,大量美洲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据历史学家全汉昇估计,作为世界上主要的产银地,西属美洲所产银约有1/2流入中国,在1571-1822年间,流入中国的西班牙银元高达2亿多元。吴承明则估计1650-1833年间有1.38亿两银(约4310吨)从西方流入中国;而同期中国国内银产量仅有7000万两(约2190吨)。
不仅是丝织品,中国也垄断了近代早期的世界瓷器。据估计,中国输出的瓷器中,约80%多的中低档瓷器输往亚洲各地,16%的高档瓷器则输往欧洲,不仅是因为欧洲较为富裕,也是因为只有高利润才能填补远途贸易的成本。即便运到欧洲后价格大涨,中国货仍然*竞争力,研究瓷器的德国学者Christine Moll-Murata认为,从17世纪到19世纪初期,欧洲的瓷器制造业能发展起来,都是在中国内乱的间歇,一旦中国局势安定下来,欧洲的制瓷业就衰退,因为本地瓷器竞争不过中国货。
如果说此前是因为西班牙等国在制造业上落后于中国,那么后来,欧洲人又发现,自己富强以后也仍然难敌中国货的竞争力。1752年,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在《论货币》中指出,一个国家富裕起来后,其财富本身就会使之丧失竞争力,因为穷国能够对它实施低价倾销,迅速抢占其市场,这样,最终低工资的亚洲国家将接管欧洲的整个经济。此前他就曾对友人表达了这样的担忧:
“距离遥远是中国与我们通商的一个切实障碍,把我们的贸易局限在少数几种商品上,并且抬高了这些商品的价格,这是由于长途运输、垄断和征税造成的。一个中国人工作一天只挣得一个半便士,而且还非常勤劳。假如中国在地理位置上就像法国或西班牙那样靠近我们的话,那么我们所用的每一件东西都将是中国货,直到货币和价格达到同等水平,即达到它与两国的人口数量、勤劳程度和商品数目都成比例的水平。”
由此也可以看出,休谟认为,中国货之所以有这么强大的竞争力,说到底是因为三个因素:人多、勤劳、货物品种多,使得中国商品又多又好还便宜。那这背后的秘诀果真如此吗?
02、中国货的秘诀
中国之所以人多又勤劳,说到底其实都是因为同一个原因:在一个农业文明中,要谋生就得精耕细作,而精耕细作增加的产出又能养活更多人。
在近代以前,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远远走在任何其他文明之前,能通过高度熟练的集约劳动,充分而高效地利用各种资源。但仅仅如此还不足以催生出品种丰富、价格亲民的大量商品,这还得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那就是需求旺盛的大众市场。
在欧洲中世纪,社会阶层之间壁垒分明,城市里的工匠所生产的商品,实际上大多是供贵族所使用的,平民百姓既用不起,也不准用——14世纪的英国自耕农不得穿丝绸、戴戒指、纽扣,因为纽扣在当时也是非常时髦的新事物。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少数上层贵族才有消费能力,因而当时西欧“从东方国家所得到的东西几乎只是少数奢侈品”。
不仅如此,手工业行会的力量极其强大,如美第奇家族统治下的佛罗伦萨是这座城市最辉煌的年代,然而非行会的丝织品被一律禁止,即便是其控制下的乡村地区也是如此。等到了17世纪,贵族由于长期持续的萧条,渐渐地没钱购买昂贵丝织品了,但佛罗伦萨商人却不得在城邦内生产廉价丝织品,因为他们继续受限于行会规则。
当然,中国古代也有行会,也有对平民消费奢侈品的等级限制,但却远没有西欧那样严格,国内消费也一向注重百姓日用。这在货币制度上就能看出差异:欧洲一直是贵金属货币,如果购买普通日用品会极为不便;但中国则相反,战国时期出现的铸币就都是铜铁制成的大量贱金属货币,适用于广泛的日常交易和基层市场,直到明代中后期输入大量美洲白银后才开始转用银子为货币——即便如此,16世纪中叶户部尚书葛守礼仍上疏提倡钱币流通,理由是“用银极不便于小民”。
中国的贵族社会在中晚唐就已瓦解了,至迟到宋代就已确立了平民社会,整个社会生产就旨在满足普通人家的多样化需求。在朝廷的节俭政策下,甚至连朝廷祭礼也禁用金玉铜器,而以价廉的瓷器替代。也就是说,中国可说是最早出现的一个以满足日用大宗消费为取向的社会,欧洲在工业革命满足大众消费之前,在三百年里都是无力与中国商品竞争的。
归根结底,中国不仅仅是“人多”,而且消费主体更远不像当时其他社会那样仅限于一小部分上层,这就极大地刺激了消费品的大众化生产。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世界经济通史》中指出:“走向资本主义的决定性作用,只能出自一个来源,即广大群众的市场需求,这种需求只能通过需求的大众化,尤其是遵循生产上层阶级奢侈品的代用品的路线,而出现于一小部分奢侈品工业中。”像纽扣、茶、咖啡,在早期都曾是上层享用的奢侈品,但到后来价格不断降低,最终成了大众消费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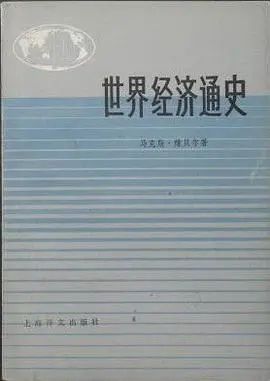
《世界经济通史》
[德]马克斯·维贝尔(韦伯) 著,姚曾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明清中国社会也正是如此,何况又没有欧洲那样严格的行会限制,于是商品价格很快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日趋低廉。据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记载,制袍服的姑绒,明时每匹价值银百两,到康熙时已降至一二十金,次者仅八九分一尺,下者五六分,“价日贱而绒亦日恶”;瓷器在明末崇祯时最上者三五钱一只,到康熙初年“忽然精美”,但价钱却下来了,最上品也不过每只一钱银;连原本西洋产的眼镜,早先每副值四五两银,“顺治以后,其价渐贱,每副值银不过五六钱。近来苏、杭人多制造之,遍地贩卖,人人可得,每副值银最贵者不过七八分,甚而四五分,直有二三分一副者,皆堪明目”,一样能用。
这看起来很美,也能让百姓过得更体面,然而中国却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引爆工业革命。由于在这样一个平民社会中,普通百姓习惯了生活在基本线上,讲求平均,其结果便是很难产生必要的资本积累。跟西欧、日本的长子继承制不同,中国的诸子均分制也不利于财富集中,而财富集中才能有剩余资本用于投资。经济学家薛暮桥1937年研究农村经济时就发现,贫农没有力量改进农业,而地主富农又不愿意扩大经营,社会生产于是难以取得突破。
刘志伟在研究清代经济史后发现,对中国人来说,生产商品赚钱只是手段,其真正的目的不是“投入市场后可能带来的利润,而是维持家庭成员生计的需要”,以便“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更多人口”。动机既是糊口而非利润*化,也就不注重技术门槛,而更容易降价以图薄利,这就带来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大量劳动作同质化竞争,产出的东西利润越来越薄,陷入了“内卷化”,累死累活却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华人甚至到了海外仍然如此,华侨*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说:“缅甸以产米为大宗,米厂百多家,华侨占有六成之多,买粟卖米,互相竞争,绝无联络,致难于获利。”
这里*的问题在于:中国商品虽然攻占了许多海外市场,但由此带来的利润却并未落入中国商人手中,进而使产品和技术升级换代,反而是陷入了内卷化的恶性竞争。最终,当西方凭借工业革命兴起时,中国人终于迎来了严峻的挑战。
03、重塑中国货的竞争力
1760-1840年间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原先曾*全球的中国商品,越来越难以抵挡洋货的冲击,节节败退。
西方列强之所以能成功,当然首先是其凭借武力强行取得的不平等待遇。由于关税不能自主,直到1901年,中国商人在北京销售国货要缴5%的税,但洋货却只要3%,这当然不利于国货的价格竞争力。然而,不可否认,列强在资本、技术上也有强大的优势,由此带来的强大工业化生产,极大地抵消了中国商品的价格优势。到了18世纪末,一名欧洲女工纺出的纱线,在印度需要300名妇女才能完成,可想而知,这极大地降低了其生产成本。
1816-1829年间,美国新式纺织厂创设极多,布价由30美分降至8美分,结果中国土布的海外销路锐减,而欧美棉布开始大量倾销中国,到1830年首次出现逆差。像这样的故事,后来一次次在不同领域出现,即便中国人再勤劳,落后的手工业生产渐渐不敌国外机械化工业生产下价格低廉的洋货。
更重要的是,原本像瓷器、茶叶这样的中国商品在海外畅销,依靠的是在工艺等方面的垄断性,在19世纪初的英国,仅茶叶贸易所创造的利润就相当于其他中国商品的利润总和,正因此,欧洲人想方设法打破了这种垄断,先是在欧洲仿制瓷器成功,然后英国人又在印度、斯里兰卡成功引种茶树,这就大大减少了对中国货的依赖。到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和外贸同步衰落,份额不断下降:1913年,中国出口在世界的份额只剩下1.7%,1952年只有1.6%,1979年更降到1%。
不过,中国人也学得很快。清末维新派麦孟华曾检讨:“夫中国制造,举办非难,例之泰西,实有三利:物产蕃衍,运近货廉,一也;人性勤奋,工奋价贱,二也;西国成法,便于仿行,三也。能行公司之法,泰西之获利五者,中国之获利十。”也就是说,只要能善于学习西方的现代公司制度,中国制造可以有双倍于西方人的获利。
1912年后,中国新式纱厂出产的棉货开始对外出口,而正如赵冈等所著《中国棉纺织史》所言,“中国棉货能打入国际市场,不在于质优,而在于价廉。”1916年,美国商务部报告中国棉纺织厂的情况,发现中国劳动力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便宜,无数工人昼夜三班倒,周日也只有12小时休息时间,而工资仅为每天10美分,连印度孟买的棉纺厂主也害怕中国的竞争,因为和他们不同的是,中国的棉纺织产业“完全不受工厂限制性法规的约束”。
这已经预示了后来人所共知的故事:一旦中国人觉醒过来,在采纳现代技术的基础上,有效动员自身高素质的庞大劳动力,很快就变身为无可匹敌的世界工厂。这在近些年来又唤起了西方人脑海中某种“面对庞大数量”的基本恐惧——早先是“人海战术”,现在则是“潮水般的中国商品”向全世界吹响了冲锋号。
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中国商品是否足够便宜,而是能否避免历史上的价格恶性竞争的内卷化陷阱,通过创新和技术升级,爬升到产业链条上利润率更高的位置。和以往一样,这并不只是中国人能不能生产的问题,而是国内是否有一个庞大的富裕阶层来消费高价值物品,否则就算生产出来也卖不出去。
现代研究已经表明,大多数成本的节约是通过细小的、无形的、累积的改进实现的——这是中国人相当擅长的事,但正因为历来注重节流而非开源,开创新的消费欲望、改进技艺、提升品牌并获取更高额利润的能力,却是中国商业文化较为缺乏的。在成为“世界工厂”之后,如何更上一层楼,打破“中国货只是便宜货”的刻板印象,这是新一代中国人所需要认真面对的挑战。
参考文献:
[1][瑞士]塞尔日·米歇尔《中国的非洲》,孙中旭等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95页
[2]罗丰《蒙古国纪行:从乌兰巴托到阿尔泰山》,三联书店,2018年,第368页
[3]冯明珠《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1774-1925》,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107页
[4]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8页
[5][美]穆素洁《中国:糖与社会——农民、技术和世界市场》,叶篱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1页
[6]李伯重《早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载清华国学院编《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5页
[7]崔瑞德、牟复礼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史卫民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382页
[8]前引林仁川著,第220页
[9]前引李伯重文,载《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第132页
[10]前引李伯重文,载《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第124-125页
[11][英]伊斯特凡·洪特《贸易的猜忌:历史视角下的国际竞争与民族国家》,霍伟岸等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63页
[12][美]尤金·N.安德森《中国食物》,马孆、刘东译,刘东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13][美]格林菲尔德《*的红》,唐富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页
[14][法]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上卷“依附关系的成长”,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31页
[15][美]理查德·拉克曼《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近代早期欧洲的精英斗争与经济转型》,郦菁、维舟、徐丹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5-126页
[16]葛氏原话是:“以天下省分,有旧钱者则用,无者遂只用银。然用银极不便于于小民。且如山陕,即隶卒而下,不得食菜,通衢大邑,无卖饼之家。行路者,必自饮爨而后得食,以不行钱故也。”见葛守礼《葛端肃公集》卷三《广铸制钱足用疏》,出自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黄山书社,2013年,第84页下栏
[17]蔡玫芬《官府与官样——浅论影响宋代瓷器发展的官方因素》,载严娟英编《台湾学者中国史论丛•美术与考古》(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587页
[18]王家范《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91页
[19]马克斯·维贝尔(韦伯):《世界经济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62页
[20]叶梦珠《阅世编》,来新夏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
[21]薛暮桥《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农业出版社。1980年,第23页
[22]刘志伟《清代经济运作的两个特点——有关市场机制的论纲》,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第170-171页
[23]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岳麓书社,1998年,第396页
[24]董玥《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三联书店,2014年,第117页
[25][意]乔吉奥·列略《棉的全球史》,刘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序言第1页
[26]赵冈、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117页
[27][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孟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5页
[28]前引李伯重文,载《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第132页
[29]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五
[30]前引赵冈、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第119页
[31][美]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徐轶杰、杨燕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第349页
[32][美]乔尔·莫基尔《富裕的杠杆: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本文由投资界合作伙伴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授权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editor@zero2ipo.com.cn)投资界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