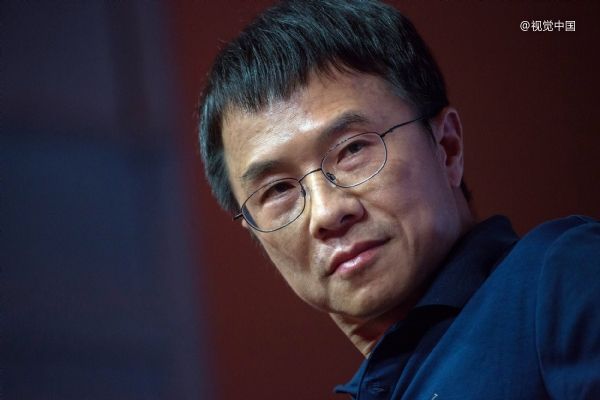一个现象是,一部分跑在行业头部的创业公司,背后创始人的成长背景高度相似。
他们的父辈大多在90年代为了改善家庭生活而“下海”,置办起以外贸代工、原料加工等传统制造业为主的工厂,成为改革开放后创业浪潮中的一分子;
他们早早通晓了商业领域中的供需关系,耳濡目染——尽管多成长于父辈创业最忙碌之时,因父母无暇照料,儿时多被送到寄宿学校或亲戚家,但等回到父母身边,迎来的也并非是和父母去游乐场的机会,而是跟着去工厂里、酒桌上;
他们多被父母安排了一条“找个班上”的安稳轻松路,创业?继承家业?算了,太苦了,创一代父母在吃够了创业的苦后,希望的恰恰是子女不再重复自己的老路,毕竟,要么有些父母年纪尚可,还有精力自己打理,要么有些产业看似已走向夕阳,再无起势。
但,他们偏偏选择了父母们最不希望他们走的那条路。
姑且将他们“粗暴”地定义为“厂二代”。
这些“二代”们在创业这条路上惯性但又“忤逆”着前行。但比起父辈,他们大胆、松弛、且更豁得出去。
创业之路上,既要有笃定感,又要敢下注。苦自然依旧是苦,但他们的筹码,显然丰厚得多了。
这里是「尺度」栏目,记录新生代创新者的真心话与大冒险,推陈出新才是商业未来的尺度。
安稳、轻松?没劲,太没劲了
2009年,25岁的蔡姗妮辞去了在杭州一所大专内的教职,要知道,放在当下,那是多少高材生挤破脑袋去竞争的一席职位,但蔡姗妮嫌那工作过于清闲,没意思。
在回到老家绍兴诸暨的那一年内,她也曾帮忙打理过家里的生意——跟着收钱或是接待客户。因为无论自家的袜子原材料生产企业还是婆婆家的印染工厂,都属于传统工业体系下一本万利的生意,运行平稳,年入上亿,根本不需要她过多插手。她觉得自己就像个“没事可做的千金大小姐”。
没劲,太没劲了。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她需要能发挥出个人价值、做有成就感的事情。
蔡姗妮毕业于中国美院服装设计专业,她想了想,做袜子吧,既然都已经在这样一个被资源包围的环境里了。
诸暨大唐,蔡姗妮生长的地方,是一个在改革开放后围绕袜业生产而崛起的小镇,被称为“袜业之都”。据近两年的媒体报道,这里每年能产出250亿双袜子。从最早人均日产几十双的手摇袜机时代起,蔡姗妮家里就做起了袜子生意,所有亲戚都在这条产业链上,原材料、代工厂等等。所以当她创业初期因为单量少没工厂愿意接时,也都是靠着这层关系才得以生产。
为什么又要做袜子呢?整个家族都对这个行当厌烦极了,他们觉得这简直是一种倒退,“好日子都已经开始了,又要去过苦日子。”
想法起源于一次上海的经历——蔡姗妮在美罗城看到了一家名为“趣趣安娜”的袜店,日本的品牌,一双袜子39元,但仍旧客流不断,她在那看了两个小时,不解,“为什么人家可以把袜子做得那么好看,我们大唐只能做这么low的袜子?人家一双卖39块钱,我们一双卖3毛钱?”其余时间她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大唐这个行业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些改变?”蔡姗妮要做一个中国的“趣趣安娜”。
做品牌是她从大学时就生发的想法,父亲告诉她,那首先你要注册一个商标,那时的蔡珊妮酷爱喝焦糖玛奇朵,于是取了意大利语Caramel Macchiato中的前两个单词,组合成Caramella卡拉美拉。
她的计划从开一家袜子小店开始,诸暨市区的家附近,开车2分钟,前后投入了近50万,却发现在周边的工厂里根本选不到袜子,“他们都是做那种特别差的涤纶袜子,要不就是那种仿耐克阿迪的袜子。”她只能四处去淘高端一点的外贸尾单,卖完就没。
无论形式还是规模,都无法支撑蔡姗妮的品牌梦,而且赚的钱也都进了房东的口袋。她必须另辟蹊径。
自己设计。但自古以来国内就没有袜子设计这一工种,蔡姗妮学的也是服装设计,只能自己试着设计,然后到厂里找机修工师傅验证更改。她也许是国内*个专业做袜子设计的人,后来公司里的设计师都是她招来的美工自己培养的,此前还曾有一名研究设计的教授专门来取经。
2012年,蔡姗妮设计了一款花边袜,卖了20多万双,成为了卡拉美拉的*个爆款。那是她每天开着跑车载着三大包袜子去一个婆婆家手工缝制花边赶出来的,那个画面蔡姗妮现在想来也觉得滑稽而可爱——一辆昂贵且精致的宝马Z4后备箱被大包袜子撑得张开大嘴,只能用一根绳子胡乱勒住盖子。2013年,荧光配色成为时尚界的风向标,蔡姗妮也顺应潮流推出了一款荧光袜,零售12元,这在当年的国内市场已经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高价了,年销售50多万双。
蔡姗妮迎来了创业以来的大爆发。她记得母亲帮她收拾车时,从里面捡出的零钱就有十几万。
累吗?当然。这是“大小姐”很少吃到的苦,但也是蔡姗妮难得感受到充实与成就感的时光。
很显见一个共同点是,在这些创业的二代们身上,赚钱已不是他们所追求的*要素。
他们想要的更多是颠覆当下的某种形势,比如改造传统工业生产方式,或打造出更具自我风格的品牌或产品,放大自身价值。这种追求,与渴望获得利润回报,改善家庭环境的父辈相比,更多了一层理想滤镜。
张志乾也是这样一个“叛逆”的创业者,这位1995出生的年轻人本来被父母安排了一条安稳的人生路——好好学习→考入医学院→成为一名医生。创业?算了,太苦了。
他之前也确实走在这条路径上,但在中山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本博连读的第三年,张志乾偶然接触到了合成生物,一个在国外热门,但国内还属于前沿到未成型的概念,“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改变各行各业的方向,会替代传统生产方式”。
张志乾对生产方式的变化是有敏锐感知的。千禧年初,他的父母在山东成立了一家大宗产品的制造企业,在这样的成长背景中,张志乾先于其他同龄人感受到了彼时工业化生产的高效与便捷,那种甚至不需要高科技含量的机械生产快速地填补了当时日常生活中匮乏的物质需求。这种感受是奇妙的。
但没过几年,工业化发展过剩之后,环保部门开始严查并关停这类传统工厂。他更深刻地感受到,制造业发展与时代匹配的重要性。传统的工业生产,未来的趋势一定是更高效、低耗的。所以,当他遇到合成生物后,张志乾预感到,新一轮的生产方式变革要到来了。
所以,后来张志乾组队去国外参加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国际科技赛事即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iGEM),先后获得总决赛金奖、*治疗奖、*新组成型生物模块奖。第二年,他就在校外组建了一个专门的实验室。
哦,这跟父母给他安排的既定人生路当然是不一样的,所以组建实验室的钱他跟父母陆陆续续磨了两年才得以维持。2020年底,张志乾的团队搭建出兼具量产和普适性的Tidetron Altra平台型菌株库,跨越了从实验室到工厂规模化量产的鸿沟,实现以生物发酵等方式在工厂规模化量产各类绿色、优质的原料产品,这些材料可应用于美妆、食物等领域。
父母也曾劝他是否要将项目“卖个小钱”?但想了又想,张志乾还是想自己做,2020年下半年因实验需求,张志乾已经注册了一个公司,并拿到了一笔投资。从投资人的角度出发,如果这个事儿做成了,会对传统行业有颠覆性的改革。“可能基于对我的支持,以及看到我的坚持,他们愿意帮我去试一下这件事儿。”2021年,张志乾用半年时间组建了一支团队,并在山东建成了一个生产工厂,态创生物正式投入运营。
张志乾想起前阵子几个同龄人讨论起他们这个时代的人的多样性,大家有一个共识,“很多创业者其实就是为了满足某一个很小的群体的需求。”比如他的一个同样身为“厂二代”的朋友,创业做了滑雪板,只是因为他觉得市面上的滑雪板都不好用,想自己做一个觉得好用的品牌。
90后的林元创业也是起于类似的初衷,他热爱户外运动,但觉得国内并未出现一个足够好的相关品牌,于是选择在此领域中开创一番天地。
他父辈在2000年做起服装的外贸代工生意,赶上了改革开放后的创业黄金三十年,年入上亿。
林元从小被送往国外,父母的盘算是在他学习艺术毕业后做些画廊相关的工作,慢且悠闲。但在被各种富二代的包围圈内成长,林元还是忍不住想做番大事。他先是踩着红利的尾巴尝试了一把互联网创业项目,后来又看到了国外户外品类的兴起,判断国内大势也要到了,于是准备入局。
已经吃过一次互联网的亏了,父母不想让他再折腾了,为断掉林元创业的念头,甚至故意不给他启动资金,希望能把他逼到国外或者直接找个班上。但他们低估了儿子的创业决心,家里不给钱就出去找呗,很快,林元就拿到了一笔数百万美元的投资。
既已开局,父母也无其他办法,不过好歹是相对熟悉的领域,他们似乎更踏实了些,只得支持。
大胆、冒进,以及豁得出去的底气
蔡姗妮感觉母亲总是很忙,“屁大点事都要到她这儿”,蔡姗妮总说她,“做了这么多年老板娘都不会管人。”所以母亲的袜企规模也一直没有做大,永远固定在二三十人。
而蔡姗妮呢,2014年起,便开始放权,请人进行管理,目前她的企业已经扩展到了130多人。
相较之下,除去林元家里的企业外,文中二代创业者们的父辈企业规模都并不算大,甚至发展几十年都不如二代们这几年发展起的规模,一是限于上一代管理者保守的企业管理方式,另外则是两代人对于资本认知的差异,以及对企业发展的*追求上的不同。而这也致使,在子女的创业过程中,除去对聘任人员的经验判断外,上一代很少有能被复用的资源传导给二代创业者。蔡姗妮说,现在父母能给予她*的帮助,就是帮忙照顾好家里的孩子。
2016年,蔡姗妮把目标客户从原有的B端转向C端,这是家族生意里从未触碰过的生意链一端,琐碎而艰难。“品牌还是要做,不然你很难在这个行业里面长存。”在他们这个被袜子生产包围的环境中,蔡姗妮当然知道,在这里打价格战全无优势,她的突围只能靠设计和品牌。
蔡姗妮招募团队开始在电商平台发力,开自己品牌的天猫店等,但这当然会触碰到长期合作的分销商的利益,被分了蛋糕的经销商们纷纷抗议、退出。这是一段困难时期,但很快,卡拉美拉在C端就立住了脚。2017年,店铺积攒了100万粉丝,第二年双11,卡拉美拉就在天猫卖了1200万元。这个品牌总有爆款出现,到了2018年,一组4双的童袜最高能卖到49块。
兰宇轩是我们所接触到的厂二代中,*一个创业不受家长阻拦的“厂二代”创业者,也是最年轻的一位,1997年出生。
去年2月,刚刚24岁的兰宇轩便参与创立了微构工场,一家专注于嗜盐微生物的改造和工程化应用的企业,这家公司的技术成果转化自清华大学陈国强教授——一位在合成生物领域颇具权威的*,也是兰宇轩本科时的老师。
兰宇轩的父亲是国内较早一批的生物学领域创业者,研究并生产生物科研工具。在90年代的中国,那还是一个非常高精尖的领域,父亲的研究团队开发出很多新技术,但由于缺乏对专利方面的保护意识,所以很多专利都未申请。再加上父亲对于创业这件事没有更大野心,最多是希望在北京落脚,让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所以他很少在扩大企业规模上花费精力,比如,他很少应酬,因为要回家陪孩子;在同行业内几家企业先后拿到投资后,他却表现得比较“佛系”,因此公司规模二十年来一直稳定如初。那些同行业曾经营收只有千万级的公司,在资本的运作下,有的已经跑出了市值百亿级的体量。
他倒不觉得父亲对此有何悔意,但确实父亲也曾提醒过兰宇轩,“如果要创业,一定要多关注知识产权保护、融资等细节”。
他当然是注意的,相比父亲的“佛系”,兰宇轩所在的微构工场成立一年左右,已经累计获得3亿元融资。
“在思维模式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包括对于创业的目标,可能像我们这一代人的话,更多来讲不是说完全为了物质这一块了,而是希望去实现一些个人的自我价值,也希望说能够做出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来。”兰宇轩说。
他们将更多资金投入到专利的布局和研发,而这对于父亲来说是无法下手的一件事,“在没盈利之前去花很多钱去做研发,对于他来讲可能是不可想象的一个事情,至少得跑起来了,可以拿出百分之几做研发科研,而我们更多是优先把核心技术成果做出来,先把资金投向研发,以期取得*于市面的产品。”
林元和张志乾的父母也都没拿过融资,但目前,两位二代创业者都已经拿到丰厚的融资,成立仅两年的态创生物,在张志乾的主导下已先后进行了4轮融资,累计金额过亿美金。
“人家为什么会愿意把钱给你?”父辈们会担心这些资本会给子女们带来太多风险,比如“资本市场是不是有什么要求?”以及“什么时候要去兑现这些事情?”张志乾的父母所知道的常规获取资本的渠道就是向银行贷款,而林元的父母连买房都是全款。
二代们发现父辈在创业时都很在意变现周期,“他们就比较在乎周期要短,比如投入个三个月,然后能看到一些回报,而且一定是说要看到有回款,再去思考留出多少钱去做公司发展,比较踏实。”张志乾说。
而二代们则不然,他们并不会过于急切地追求盈利,而是在一定时间内进行公司的全面布局,耐心等待业务成长。而这种底气往往来自于背后富足家庭的撑腰。
“一个只见过宝马的人,也做不出来超跑”
二代们身上有一种在普通创业者身上鲜见的松弛感。
比如他们很少因为某一笔生意而向难缠或无礼的合作方低头。
蔡姗妮曾遇到一位外国客户,总是挑挑拣拣把店里弄得乱七八糟,前一天谈好的合作后一天又要变卦,还要求15天后结账,蔡姗妮的火一下顶到了脑门,“我认识你是谁啊?货不发了,你们爱咋咋地。”她才不在乎这一单生意。
”我爸经常说弄不好又怎么(样)?我们家有两座金山,能管你这辈子生活无忧;我公公经常说我们染色厂现在房租都有300多万一年,你啥也不干下半辈子就不愁吃喝了。”这就是蔡姗妮可以“耍脾气”和采取冒进措施的底气,类似于2016年不顾分销商反对强行转向C端,“我觉得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豁出去敢放手去干嘛,不会抠搜搜。”
做户外品牌的林元不也是这样?“说实话,在这两年选择做这个品类已经算胆够大了,因为它都不能称为一个标准的投资圈消费品牌,对吧?”林元说,“能进入一个没什么快钱的赛道的人,他要不就是对于钱没有追求,要不就是足够的底气和与别人不同的预判和信心。”
“你属于前者还是后者?”
“我暂时是属于后者。”
兰宇轩也直白地表达过类似的情况,因为父亲早期创业积累下的财富而使他在创业初期无需为收入有任何担忧。
蔡姗妮的企业已成长为诸暨大唐的龙头,工厂内的2000多台机器,能够让她年产5000万双自有品牌卡拉美拉的袜子,同时帮其他品牌做代工,一年可产出几亿双袜子,双管齐下的经营模式使得蔡姗妮的企业年收入已超3亿,这一体量也早已超越了父辈。当初一直念叨着说最后还是要家里给她收拾烂摊子的婆婆妈妈们,也在这两年逐渐息声,踏踏实实帮她照顾孩子,以及偶尔打理下仓库。
蔡姗妮知道为什么长辈对她会有这种预判,“我从小就是一个不怎么成器的孩子,确实上学成绩一般般,也不是特别着调,让我干事情也没有什么能干成的,我不是那种特别上进的小孩。”
他们都是成长于父母最为忙碌的创业初期,自幼与父母聚少离多,多数被送往寄宿学校,即便见面也都是陪着父母一起忙生意上的事。这种粗糙且类似的成长经历,也让他们早早在家庭氛围中耳濡目染了许多商业世界的法则。
张志乾是小学三年级后被送到寄宿学校的,在那之前他经常被忙碌的父母带在身边,一起吃住在工厂或者一起出席应酬酒局,寄宿之后回家的周末则要跟父母开着货车四处送货,在这种沉浸式商业体验中,张志乾很快就先于他的同龄人知道了什么是供需关系。
“小学有卖零食的,我会在大家不去买的时候提前囤一些需求量大、经常买不到的零食,等大家都去买的时候,可能要排队,我就把价格加高一点,赚差价。”做这些事的时候,张志乾上小学四年级。
兰宇轩也做过类似的事,比如小学时的跳蚤市场就是他的经商圣地,他经常在前一天临近结束时去市场收购那些被同学急着出手甩卖的低价商品,比如从20元降到2元的玩具,第二天开场时再以20元售出。
创业的种子从兰宇轩小学时就已经在心生根发芽了。除去在家看到的人物传记外,兰宇轩也会被父亲的公司氛围所吸引。千禧年初,电脑还是个稀罕物,私人家里少有,而兰宇轩父亲的公司有,他时常跑到那儿去玩儿电脑。正赶上行业进入快车道,父亲公司的几十人经常开会、讨论,而且谈论的内容都很专业,“我也听不懂,我觉得这种好像很专业,这东西还蛮酷的。”很多人共同为一件事而努力的场景就更让他着迷了。
后来,因在父亲影响下对生物产生极大兴趣的兰宇轩考入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并进入微生物实验室,师从合成与系统生物学中心主任陈国强教授,当然这也是对这一领域相对熟悉的父亲给出的建议。此后,兰宇轩也在微构工场创始团队的邀请下,参与到公司的创立过程中来。
林元则从小被送到国外的一所国内二代们聚集的私校,小时候犯事儿学校发给家长的邮件其实都到了他手里。
“其实目前为止创业成功两大点,一种是老板团队都是草根,一起奋斗,一种就是二代跟二代互相开始做一些生意,大家也可能成功。”林元说平时二代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鄙视链,更多的还是资源共享。
“我们也是普通人,我们也是好好工作的人。不要妖魔化我们。”林元因为“二代”这个身份以及受到了足够多的大众偏见与社会议论,比如做好了就说因为你有资源,没做好那你读这么多书连父母都不如。中学时,林元还会对自己的身份遮遮掩掩,而现在他反而不在意,因为得承认,这就是你比普通创业者多出的那一块优势。
很显然的一点,林元的品牌开始投入量产后,家里的工厂也成为了他品牌部分产品的代工厂,以成本价进行交易。你看,这就比普通人要省掉多少成本。
“我们这一代创业*的优势,就是好的不好的东西我都见过。”林元说,“如果一个人只以为CHANEL是*的香水,那怎么能做出来好的香水?一个只见过宝马的人,让他去做超跑,他也做不出来啊。”
不过,他现在仍担心投资人会因为他的“二代”身份,认为他创业只是叛逆公子哥的一次“玩儿票”行为,最终还是会回家接班,因此影响到品牌融资与发展。哪怕他无比确信自己的认真与决心,“但有些但流量党和连续剧都这么写。”
目前的成果是,林元的品牌已逐渐步入正轨,上线三个月便冲到了行业第四,且销量稳步增长。
(应受访者要求,林元为化名。封面来源视觉中国。除标注外,文章图片均来自视觉中国。)
【本文由投资界合作伙伴36氪授权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editor@zero2ipo.com.cn)投资界处理。